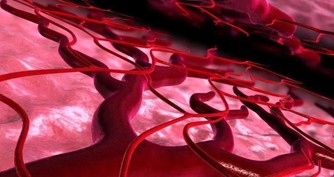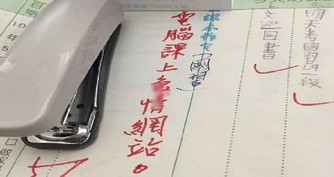|
|
|
一個腫瘤已經毀掉了她的容貌、睡眠和一半聽力,未來可能還會奪走她的生命。 觀看數:1323 人
顱底腫瘤女孩重生記
原標題:重生

鷹哥說自己當時有些緊張,閉上眼,心裡卻忽然湧起一陣喜悅。她甚至期待手術刀碰到皮膚的瞬間,那是她在過去幾十個失眠的夜裡最盼望的一刻。她很清楚,只有這些冰冷的器械才能救自己的命。
“鷹哥”是個女孩,有一頭及腰的長發。
進入手術室前,她剃了光頭躺在轉運床上,與正在給自己打鎮靜劑的護士開著玩笑。
| sponsored ads |
| sponsored ads |
15分鐘後,她將接受一台超過8個小時的頭部手術。一個巨大的腫瘤佔據了她顱腔四分之一的空間,腫瘤已經毀掉了她的容貌、睡眠和一半聽力,未來可能還會奪走她的生命。
手術的主診醫生張家亮沒有過來看這個病人,這是他做了20多年外科醫生養成的習慣。他不想讓本就緊張的病人術前再有情緒波動,何況眼下這台手術比以往都要復雜、凶險。
住院前,鷹哥和其他24歲的姑娘一樣愛美。
| sponsored ads |
| sponsored ads |
她習慣在出門前涂口紅、描眼線,穿裙子一定要配上高跟鞋。她皮膚光潔,眉眼清秀,夢想著未來開一間咖啡廳。

鷹哥病發前舊照 鷹哥供圖
這個廣東姑娘從小就離開父母,跟著爺爺奶奶留守在鄉下老家,“一直活得血氣方剛”。她曾是學校女排隊的主攻手,比同齡的孩子高一頭。因為經常為同學打抱不平,名字還裡有個“瑛”字,她被身邊朋友“尊稱”為鷹哥。
| sponsored ads |
| sponsored ads |
去年5月的一個周三下午,張家亮在辦公室裡見到了鷹哥和她的父母。那時她已經跑遍了廣東幾家著名的大醫院,但沒人敢收治她。一個多月內,她聽到最多的話就是“太晚了”。她把北京當作最後的希望,比任何時候都更期待在醫院擁有一張自己的病床。
張家亮從醫以來,見過的第二大顱底腫瘤就在他面前女孩的腦袋裡。
| sponsored ads |
| sponsored ads |
腫瘤累及幾乎所有的顱底神經,包裹住麻繩一樣的腦血管。手術難度不僅在於精細度要求高,更需要多個科室協作。在北京同仁醫院,張家亮自信“身邊站著全國最牛的五官科大夫”。
這位醫生把鷹哥母女支走,留下父親一人溝通病情。鷹哥回憶,她在門外就像等待審判,攥緊拳頭,手心不停冒汗。
| sponsored ads |
| sponsored ads |
一個月後,當她再一次走出同仁醫院神經外科病房時,手裡已經握著“重生”的“判決書”。
-1-
2017年5月16日8時30分,鷹哥被推進手術室。她躺在空蕩的房間中央,裹著厚棉被,暴露在外面的頭皮能感覺到冰涼的空氣。護士開始檢查手術器械,那些金屬制品碰撞在一起,聲音很輕,但在安靜的手術裡顯得很清晰。
她說自己當時有些緊張,閉上眼,心裡卻忽然湧起一陣喜悅。她甚至期待手術刀碰到皮膚的瞬間,那是她在過去幾十個失眠的夜裡最盼望的一刻。她很清楚,只有這些冰冷的器械才能救自己的命。
8時45分,醫生一個接一個走進手術室。
口腔頜面外科主任劉靜明是其中之一。鷹哥來同仁醫院的那個下午,劉靜明接到了“老朋友”張家亮的電話,要他有時間過去看一個病人。
同仁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和神經外科的醫生辦公室都在病房樓一層,步行只需要3分鐘。十幾年來,除了平時工作上的合作外,兩位醫生經常在樓道裡碰面,空閒時會停下聊幾句,或者出去喝一杯。雖然各自專注的領域不同,但他們在日常中積累出信任,“凡事隨叫隨到”。
在張家亮的辦公室,劉靜明第一次見到了鷹哥。用他多年的經驗判斷,小姑娘左臉面神經損傷明顯,導致面癱。
他戴上眼鏡,把臉湊近觀片燈,患者腦部的核磁共振影像顯示,一個7釐米×10釐米×12釐米的腫瘤佔據顱腔,形狀就像一個大芒果,包裹住顱內60%的血管和神經。
“呵!”劉靜明對著片子驚嘆,他動過刀的腫瘤有成百上千個,但眼前這個腫瘤卻讓他有些頭疼,“涉及的區域太多”。
張家亮猜到了劉靜明的反應,他清楚這台手術的風險。對這些早已名聲在外的外科醫生來說,“誰也不願在別人的手術上坑自己一刀”。
“腫瘤從上到下分別涉及神經外科、眼腫瘤科、耳鼻喉頭頸外科和口腔頜面外科。”張家亮摸著自己的臉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解釋,“每個科室的醫生切除一部分腫瘤,但不管哪個人出了問題,後果都要大家共同承擔。”
這個不斷生長的腫瘤一直藏在鷹哥的腦袋深處。高中時,她就經常失眠,有時早上醒來左臉會突然麻木。因為父母不在身邊,她不想給爺爺奶奶添麻煩,就把這些“不痛不癢”的小事壓在心裡。在身邊人眼中,她就是個愛打排球、“一年不會感冒一次”的健康姑娘。
再往後,她開始經常偏頭痛,痛到“想拿塊石頭砸自己腦袋”。和以往一樣,她沒有把這些感受告訴任何人,每次忍過疼痛之後,她又“滿血復活”,出現在大家面前。
大學做畢業實習時,她曾在公交車上暈倒兩次,其中一次甚至被司機趕下車。她記得那天廣州下著雨,她在路邊打著傘蹲了很久,緩過神後又去上班。那時她以為自己只是低血糖,完全沒意識到,腳下是一根隨時都會繃斷的細線,掉下去就是“萬丈深淵”。
直到一個多年未見的親戚發現她有嚴重的“大小臉”後,她才被拉去醫院檢查。在醫學檢測儀器下,那個不知隱藏了多少年的“怪物”第一次顯出了身影。

手術前的鷹哥 北京電視台“生命緣”節目組 供圖
張家亮見過很多像鷹哥一樣的危重病人,在“一刀生,一刀死”的神經外科,他無數次與他們四目相接。
“活著。”張家亮頓了頓說,這是他從病人眼神裡讀出的同一種信息,鷹哥的眼睛也在“說”這兩個字。
張家亮記得,自己還是實習醫生時,為一例送來搶救的病人做心肺復蘇。病人是一個跟他一樣年輕的小伙子,張家亮用盡全力想救活他,但還是眼睜睜看著他呼吸逐漸減弱,眼睛失去光亮,直到眼珠上生出細微的褶皺——生命逝去了。
那是他作為醫生經歷的第一起病人死亡。他記得自己走出醫院,春天的陽光灑在路上,街道熙熙攘攘,一旁的公交車進站後又出站,一切平常到毫無新意。但那些細節張家亮直到今天也無法忘記,“活著真好啊,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”。
對於鷹哥,他知道再拖下去對這個被多次拒診的小姑娘意味著什麼,也許失明失聰,合不上嘴,也許劇烈的頭痛再也揮之不去。或者,在某一天她突然暈倒,墜入長眠。
鷹哥必須盡快接受手術,他等待著劉靜明的回答。
劉靜明把目光從觀片燈上收回來,他摘下眼鏡,平靜地對張家亮說:“只要你神經外科沒問題,我這裡就沒問題。”
-2-
9時,劉靜明劃下了手術的第一刀。手術刀從耳根開始,一直到下巴下方,沿著下頜骨切開一個約15釐米長的弧形創口。
42平方米的手術室裡站了11位醫生和兩位護士,除了劉靜明和張家亮,還有眼科、耳鼻喉頭頸外科和麻醉科的“大牛”。他們靜靜地圍在鷹哥身邊,緊盯著刀口,等待腫瘤暴露出來的那一刻。
在以往的合作手術中,醫生可以在手術進行到自己負責的部分時再進場,做完後就可以離開。但這一次不同,每個醫生都全程站在患者身邊。
“手術太復雜,必須所有人都在場保駕護航。”劉靜明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“我是第一刀,但一直到最後神經外科負責的部分時,我還是在旁邊關注著手術過程。”
醫生用記號筆在鷹哥的頭皮上畫出一個貫穿半邊頭顱的“十”字,術中遇到復雜情況時,可以馬上換上應急方案。
鷹哥本應按照“應急方案”進行手術,但這個方案在手術前一天被醫生推翻。舊方案采用的是“經典手術入路”:從眼睛下方橫向切到鼻翼側方,再向下沿鼻側切到上頜骨,然後橫向切到人中,再向下切到下頜骨,整個切口成階梯狀。
“通俗講,就是把半拉臉整個翻開,直接暴露瘤體。”劉靜明按照這種經典方案做過不少手術,“在醫學領域這叫‘韋伯式切口’,是教科書式的做法。”
手術前,同仁醫院的醫務處曾召集參與手術的科室舉行一次會診,劉靜明記得當時對於到底采取哪種手術入路,醫生間爭議不小。
“多科室合作,大家自然會想著盡量降低風險。”劉靜明回憶,在那次會診中,醫生最終決定采取最常規的做法。
鷹哥也參與過自己手術方案的制訂。住院後,每次醫生找到她的父母溝通病情,她都要賴在旁邊。
“我自己的事情我能決定。”她告訴父母和醫生,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腫瘤完全切除,第二是盡量保留功能,最後才考慮容貌的事。
那段時間,她把劉海留長,梳成中分,遮住變形的左臉。這個過去經常在朋友圈發自拍照的姑娘再也沒有自拍過,她也不敢照鏡子,怕看到自己的樣子。“我只想先活下來,哪怕毀容。”
她為自己設想過很多結局,最壞的是“這輩子不嫁人”,最好的是未來高超的整容技術“能把我的臉整回來”。
張家亮記得,手術方案確定了,他每天下班回到家躺下後,總會忍不住想象鷹哥毀容後的樣子。
“用取田螺肉打比方,‘韋伯式切口’是把田螺殼鋸開直接取,頜下入路是用牙簽一點點掏。”張家亮分析,新的方案會增大手術難度。“但作為醫生,如果她的腫瘤是惡性的,手術完一年或者兩年人走了,我的內疚可能會少些。現在面對一個大概率是良性的腫瘤,她臉上帶著那樣的傷疤,以後還有那麼長的路,該有多難受。”
他決定在手術前嘗試一次“游說”,說服其他醫生為患者冒一次險。
劉靜明負責打開和關閉手術創口,他相信自己能用最精細的手法縫合出最不明顯的刀口,但他支持頜下入路方案。
“她要是已婚,或者年齡大一點,我們會毫不猶豫選擇從臉上開刀。”劉靜明用手在自己臉上比劃出刀口的形狀,然後搖了搖頭。“想來想去還是覺得,以後即使長好了,(患者)臉上也會留下一條很長的線,對她未來的生活影響太大了。”
頜下入路方案最終被所有參與手術的醫生接受,手術中的每一次探尋、劃撥和切割都要比之前更加困難,新增的壓力也平攤到每位術者身上。
但他們最終達成了共識:讓這個即將沉睡於手術台的年輕姑娘,在最好的年代,展示出最好的自己。
-3-
9時30分,劉靜明戴上手術放大鏡。在2.5倍的視野下,他用手術鑷和吸引器一點點撥開骨骼、血管和神經。

劉靜明(左一)在手術中 北京電視台“生命緣”節目組 供圖
他把整台手術比喻成蓋樓,自己負責的是地基部分。其他醫生必須通過由他打開的創口,摘除自己負責的那部分瘤體。他當時要做的,是找到腫瘤最下方的部分。
一個小時後,一塊嵌在肌肉裡的淡紅色組織逐漸被剝離出來。這是隱藏了至少10年的腫瘤,第一次在燈光下,露出一部分面目。
從外觀看,腫瘤有一層包膜,“比較有韌性”。對在場的醫生來說,這是個好消息——完整的包膜意味著,切除時不用擔心腫瘤破裂。
壞消息卻接踵而至,因為術前影像不能完全確認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,醫生決定在術中切除一部分瘤體送去冰凍,做快速病理檢驗。但眼前的腫瘤讓劉靜明心裡沒底,平時他看一眼就能判斷出瘤體的供血是否豐富,這次他看不出來。
況且,為了不影響病理檢驗,切除瘤體不能用可以馬上止血的電凝刀,只能用手術刀或者手術剪,這意味著,出血量難以估計。
幾秒鐘的停頓後,手術刀的刀尖懸在了腫瘤上方。緊接著,瘤體被劃開了,血液瞬間滋到了劉靜明的頭頂,隨後下落,濺紅了他消過毒的紙鞋套。
劉靜明幾乎不需要任何反應時間,馬上用大拇指壓住了出血處,另一只手伸了出去,護士連忙把夾著紗條的布巾鉗遞到他手中。
“是不是囊液?”身邊的醫生重復問道。
“是血,是血,不是囊液。”劉靜明一邊回答,一邊把紗條按在瘤體切口處。
他一點點揭開紗布,想找出出血區的位置,但是血液不斷流出。
“吸引器跟上。”劉靜明沒有抬頭。助理醫生把一個長管放在積血區,“嘶嘶”作響中,出血被快速吸干。
瘤體內部結構顯現出來,出血的是蜂房狀的存血血供。劉靜明松了口氣,幸好不是瘤內血管出血,否則出血量還會更大。
縫針快速在瘤體上方繞了幾圈,縫線“咔”地一聲被剪斷,出血終於止住。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,但出血量超過500毫升。
10時30分,手術繼續。病理樣本取完之後,接下來就是充分暴露瘤體,進行腫瘤切除。
創口內,乳白色的神經和紅色的血管交織在一起,手術刀稍有不慎就會傷及患者頭部的某項功能。
“舌神經斷了,就失去了味覺,半側舌頭就是木的。舌下神經碰斷了,半側舌頭就歪了。如果損傷了面神經,左臉就直接塌了。”劉靜明清楚這些,他把耳機線粗細的神經小心撥開,瘤體逐漸清晰。
一個小時後,頜面的血管和神經被完全“游離”干淨。劉靜明摘下除病理樣本外第一塊真正的腫瘤,200克。
睡在手術台上的鷹哥並不知道,自己曾無比期待的這一刻已經到來。從兩個月前第一次查出腫瘤後,她幾乎每天都在經歷恐懼。
那段時間,她和父母一起,每天輾轉在廣東不同的醫院、不同的科室,期望從醫生口中聽到自己還有救的回答,但就連被護士攙扶著走進診室的老教授都向她搖頭。
鷹哥越害怕,腫瘤長得越大。它就像一個把恐懼當養分的怪物,在一個月內快速膨脹,鷹哥左臉逐漸變形,顴骨外凸,左眼球不能向外轉動,左耳失去了聽力。
每天從醫院回來,她晚上幾乎都睡不著。她在網上拼命搜索,希望找到一個跟自己病情相似的人,“希望找到一個好消息說他已經被治愈”。結果還是讓她一次次失望,她找到的最大一例腦部腫瘤只有8釐米長度。鷹哥成了一座孤島。
她說自己熟悉那種“孤獨”的感覺。4歲被送回老家,第二年弟弟出生,她一年最多見一次父母。小時候老家到父母家還沒通高速公路,她要一個人坐7個小時的大巴車趕過去。爺爺奶奶嫌電話費貴,平時想爸媽時她就寫信,然後等他們打電話回來。
在爸媽家,她住爺爺奶奶的老房間,睡“爺爺那個年代的木床”。後來床被蟲蛀了,爸爸給她換了套Hello Kitty(卡通形象名)的家具。這讓她高興了兩個星期,“盡管我喜歡的其實是皮卡丘(卡通形象名)”。
跟父母在一起,一家人有時也會去海邊散散步,但很少說話,“很悶的那種”。她無數次想親近父母,但總覺得跟他們“有距離”。
在朋友眼裡,她獨立、倔強、喜歡保護別人。確診後,她第一次強烈地期待,有人能保護自己。
-4-
12時,耳鼻喉頭頸外科和眼科醫生分別順利切除了一部分腫瘤。這時候,手術已經越過顴弓,往額頭下方區域深入,真正進入了側顱底。
在這場手術刀的接力中,張家亮的最後一棒開跑了,這也是整台手術最復雜凶險的部分。

張家亮正在為鷹哥手術 北京電視台“生命緣”節目組 供圖
剛接過手術刀,他就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:術中病理檢驗還沒有結果,但手術進行到這裡,必須決定要不要換上“應急方案”,從臉部開顱。
術前醫生最擔心惡性腫瘤,那意味著腫瘤必須被徹底切除干淨,這同時要求手術視野得到充分保證,手術入路沒有別的選擇,必須從臉部開顱。
從腫瘤對骨組織的破環程度判斷,醫生傾向認為腫瘤是良性。但術中腫瘤大量出血,又符合惡性腫瘤的特征。在等到病理檢驗這個“金標准”前,醫生不敢作出任何判斷。
“進行開顱核算。”有醫生提議。
所有人都等著張家亮的決定。他蹲在地上,眼睛與鷹哥的頭部平行,正在解剖。
他選擇再一次冒險。
“先別開顱。”他告訴身邊的同事,自己會在保證鷹哥面容和神經功能不受損的前提下,盡最大可能切除腫瘤。
張家亮把一根筷子長的鑷子深入鷹哥的額角下方。這裡是顳下窩深區到顱底的部分,視神經、面神經、三叉神經,包括動脈和靜脈,在這一區域集中。
“顱底的各種大血管特別豐富,每一個孔每一個洞都有不同的神經、血管。一刀下去,切的可能是腫瘤,也可能是動脈。”張家亮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。
顱底供血佔人體三分之二的供血量,一旦血管破裂,輕則把血止住,但血管供應的功能區功能喪失。重則血止不住,“下不了手術台”。
在顯微鏡下,鷹哥的腫瘤緊緊包裹住頸內動脈,鋼制的鑷頭被放大,佔據著大半個顯示器屏幕。
鑷頭在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動。張家亮保持蹲姿,側著身歪著頭緊盯創口內部的變化。口罩遮住了他的大半張臉,他眉頭沒松開過,向上抬眼的動作在額頭擠出一層層皺褶。
“平時手術為了降低感染概率,術者應該盡快進行手術。但這個部位就得戰戰兢兢、謹小慎微,多慢都不嫌慢。”劉靜明拉長語調說。
13時,好消息送進手術室。術中病理檢驗結果顯示,鷹哥的腫瘤是良性的,醫生們都松了一口氣。
在此之前,鷹哥曾被多次診斷為“鼻咽癌”。在廣州的最後一天,鷹哥和父母來到他們求醫的第六家醫院。見到醫生時,已經是傍晚。醫生說,她腦袋裡長的可能是惡性腫瘤,“應該早點來看”。父母不甘心,為女兒哀求著一個床位做手術。
已經在不同醫院奔波了一個多月的鷹哥再也忍不住了,她拉著爸媽沖出醫院:“我要馬上去北京,一分鐘都不想再耽誤。”
她想再做一次嘗試,把最後的賭注壓在北京的醫院。可在廣州的經歷已經消磨了父母最開始的僥幸,他們准備接受女兒就要離開的事實。
鷹哥記得,在深圳一家醫院,醫生從她喉嚨裡取病理樣本,她痛得暈倒。爸爸抱著她跑到病房,看著她往垃圾桶裡“吐了大半桶血水”。那時她雖然半昏半醒,仍能感覺到,抱著她的父親哭得顫抖。
那是她第一次見父親哭。也就是從那時起,這個男人再也不懷揣“女兒的病可能是檢查出了問題”的幻想。
身邊的親人也要放棄了,有人向鷹哥父母提議,不如把看病的錢交給孩子,讓她開開心心出去旅游,走好最後一程。
聽到女兒赴京的決定,父母猶豫了。父親告訴她,自己要先回單位請假,隨後趕去北京。從來沒有出過廣東的媽媽一直在哭,說不出一句話。
“我自己去,就在今晚。”鷹哥告訴父母,不帶一絲猶疑。
-5-
14時,張家亮仍然蹲在地上,在手術最危險的區域做最後的探索。
他再次遇到了難題。這個部位的瘤體與已經切除的部分不太一樣,他看到藏在側顱底的腫瘤沒有光滑的包膜,而是像一串長得很密的葡萄。
這要求張家亮解剖時需要更加小心,要在顯微鏡下極其精准地把瘤體和組織分離開。
“這個難度非常大,在醫學上叫‘鈍性剝離’。”劉靜明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解釋,“相當於鑽到骨窩裡了。”
張家亮要對腫瘤發出最後一擊了,他先給瘤體血管做了結扎,防止切除時大量出血,然後把一個鑷子狀的電凝刀以最慢的速度挪向了腫瘤底部。
“嘀、嘀、嘀……”手術室忽然響起急促的報警聲。
“收縮壓60!舒張壓30!”護士急忙向醫生報告。
張家亮心頭一驚,血壓太低了。手術刀停止了前進,鷹哥還躺在手術台上,整個人依然安靜,看不出任何變化。
他清楚,臨床上這樣的血壓完全可以被診斷為“低血容量休克”,他怕最擔心的事情發生。
他抬頭望向麻醉師,可還沒開口說話,對方就告訴他:“這邊我撐著,你接著做。”
電凝刀重新向深處移動,麻醉師把提前准備好的血袋掛上,鷹哥的血壓逐漸恢復正常。
“當時手術已經進行了6個小時,患者傷口暴露時間長,體液蒸發造成慢性失血,可能會引起血壓降低。”醫生術後分析,“也可能是手術時牽拉了頸內動脈,刺激了調節血壓的‘壓力感受器’,同樣會造成患者血壓變化。”
15時,手術到了最後一刻。最後一塊瘤體被劃開,高頻電凝刀觸碰到瘤體內血管時,血管脫水凝固,發出“吱吱”的聲響。出血止住了,手術室彌漫著血肉焦糊的味道。
張家亮取出了最後一塊瘤體,和先前取出的3塊擺放在一起,總重量超過500克。
被肢解的腫瘤看起來就像3塊生肉,它們離開了鷹哥的腦袋,已經永遠失去作惡的可能。
劉靜明再次上台,和他之前說過的一樣,“用最精細的手法”縫合了由他打開的創口。
最後一根縫線被剪斷時,手術室的時鐘停在了16時。
鷹哥記得自己被推出手術室後,曾有短短幾分鐘的清醒時刻。她看到一向嚴肅的張家亮對著她笑,告訴她:“臉上沒有疤,頭上也沒有。”還開玩笑說自己“第一次趴著做手術,從一樓掏到三樓。”
20年前,張家亮剛調到神經外科。當時的科室主任接診了一個15歲的小女孩,她的頭部長了一個980克重的腫瘤。那台手術轟動了醫院,老主任切掉的,是至今為止張家亮見過的最大的腦部腫瘤。
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,腫瘤最終也被成功取出,小姑娘奇跡般地活了下來。
兩年前,當時的小女孩已經30多歲了。她忽然找到老主任,說自己的弟弟今年高考,在志願表裡填上了醫學院,他立志成為一名醫生。
“這是我聽到的最好的故事。”張家亮說。
鷹哥醒來,再次看到爸爸,她發現這個男人的眼神變得很溫柔。他與女兒之前很少交流,現在每天守在床邊,不厭其煩地問“吃什麼,喜歡什麼”。
術後幾天,鷹哥雖然一直發著高燒,仍然會頭疼欲裂,但她卻說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日子。因為那是她能記得的,父母在身邊最長的一次陪伴。
“他們眼裡只有我,沒我弟弟,我不是賺大了嗎。”鷹哥笑著說。
從發現腫瘤到順利出院,不到3個月。一年快要過去了,之前的一切都化成鷹哥脖子下方一道細細的疤痕,“就像一場夢一樣”。
距今3周前,她到北京復診,見到劉靜明,開玩笑問對方“還認不認識自己”。劉靜明笑了,他說小姑娘雖然看起來完全變了一個人,但自己會永遠記住這個特殊的病號。

不久前,剛從排球場下來的鷹哥
現在,鷹哥恢復了生病前的樣子,一直困擾她的“大小臉”也不再明顯。她的耳機裡經常循環播放著姚貝娜的《心火》。她最喜歡裡面一句歌詞:重生在縫補的軀殼。
從廣州去往北京的夜班飛機上,她坐在爸媽中間。當時已經接近午夜,機艙裡的人大多睡著了。鷹哥左手握住爸爸的手,右手握住媽媽的手,然後手指用力緊扣。三個人沉默著,但鷹哥說,她從來沒有那麼幸福過。
這裡滾動定格